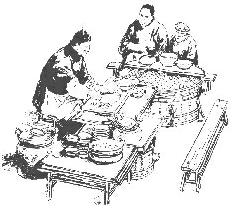
十多年以前,我刚进入报社工作的时候,有一段时间,经常去四阿婆的馄饨店。外出采访没赶上食堂中饭,就去吃一碗馄饨,和四阿婆聊会天;冬天上完晚班,去吃一碗馄饨,暖暖身子再回家。四阿婆的馄饨店,仿佛是时刻等候我的加油站。
四阿婆做的馄饨皮薄、肉多,鲜美可口,在附近有些名气。店子不大,顾客却不少,好在她做事麻利,一边煮馄饨,还可以一边下面、炒粉,有条不紊。她的老公是个瘸子,扶着一把椅子,一拐一拐地收拾碗筷。顾客少的时候,四阿婆就在一边包馄饨,如果我在,就和我说闲话。“皮要擀得最薄,像一张透明纸,肉要最新鲜的,料要足……”四阿婆最得意的就是她的馄饨。知道我在报社上班,就很赞赏:“你们读书的人,都是有出息的!”
有时候,四阿婆也讲起她的家事。她老公原来是货车司机,因为车祸瘸了脚,不能再开车,也干不了重活,家庭负担就都落在她身上。儿子二十出头,游手好闲,经常拿了店里的钱去交朋友、吃喝玩乐。店里经常只有四阿婆一个人在忙着,她老公大多数时间都在阁楼上休息,儿子偶尔从阁楼上下来往外边跑,或者从外边回一言不发上阁楼,从没见他帮店里做过事。
我觉得四阿婆很不容易,就在单位帮她宣传,要同事们去她那里吃馄饨。店子离报社近,有时候我也带同事去吃。每当我讲起工作中的一些不顺利,讲一些丧气话,四阿婆就会停止包馄饨,耐心地跟我讲生活的艰辛,一副一本正经的严肃样子。有一次我吃完馄饨,她正巧外出了,我就将二十元钱压在碗底。再来的时候,四阿婆就说:“你上次给了二十元,我给你记着账。”我忙说:“不用呢!”她就有些生气:“那怎么行,我不能无缘无故多收你钱!”
四阿婆认为我是“读书的人”,对我很信赖,经常向我打听国家出台的新政策、社会上的大事。其实只是因为她自己读书太少而高看了我,她的很多问题我也是一知半解说不清楚。她虽然很辛苦,但心态很好,经历的磨难被她轻描淡写地讲出来,就像是讲别人的事。她还心血来潮要跟我介绍对象,我当时并不着急,就谢绝了她。因为她一再宣传对方是一个多么不错的妹子,我就半开玩笑地说:“四阿婆,你还是多操心你儿子吧!”四阿婆便叹了一口气,不再说话。后来我想,我这样说,或许伤了她的心。
到了年底,上面突然来政策撤销了一批报纸,我工作的单位也名列其中。那一天,我收拾好办公室的东西,用一个大包提着,去跟四阿婆道别。我告诉她,我要去省城去找工作,以后不会来吃她的馄饨了。她听了,发了一番感慨,说好好的报社,怎么撤了,又安慰我说:“你们读书的人,走到哪里都不怕!”那天她坚持不收我的馄饨钱,我最终也没能拗得过她。
有一天我去省城找工作碰壁回来,走出车站大门,经过一排卖菜的临时摊点。小贩都是乡下来的农民,菜新鲜又不贵,因而围着很多市民。我看见四阿婆也在卖菜的行列。四阿婆告诉我,她儿子和社会上的混混打了一架,不但耗费自己一笔不小的医药费,还赔了对方不少的钱。没钱交房租,只得把店子转给别人,一家人回了乡下。但是日子还得过下去,就担些小菜上街卖……正说着,人群一阵骚乱,一辆执法车停在了路边,小贩们作鸟兽散。我转头看时,四阿婆已经跑出很远了,她挑着菜,笨重的身子,慌乱的脚步,看上去很滑稽。
大年之后,很冷的一天,我由一个熟人介绍,到邻市的报社去应聘。登上长途班车,就听到有人喊我,循声望去,竟然是四阿婆。我告诉她,我因为只有大专文凭,在省城的报社应聘屡屡失败,才去邻市试试运气。四阿婆穿着厚厚的衣服,头发一片花白,看上去老了许多,嗓音嘶哑着,脸色也不好。她告诉我,她患了病,脖子肿大,连说话都困难,这次是去邻市看病。我拿过她手里的地图,将中心医院的位置指给她看。我想,我们这里的人遇到难治的病,都是去省城,她舍近求远是因为图便宜吧。这时候,车子开动了,发动机噪声很大,我们之间隔着一条过道,就没有再说话。
路上,她从布包里拿出一个馒头和一个旧水瓶。一口馒头一口水,慢慢地吃。
到站后,我先下了车,在车站服务处问清了市中心医院的路线。但不见四阿婆出来,我进站去找,看到她的背影在另一个出口。我追出去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。
从此就没再见过四阿婆,只是常记起她逃跑时滑稽的样子和最后一次的匆匆背影。直到现在,加完晚班,我偶尔还会想起“四阿婆馄饨店”昏黄的温暖的灯光——一晃十多年过去,不知道四阿婆怎么样了?
作者:姜笑澜
编辑:陶湘